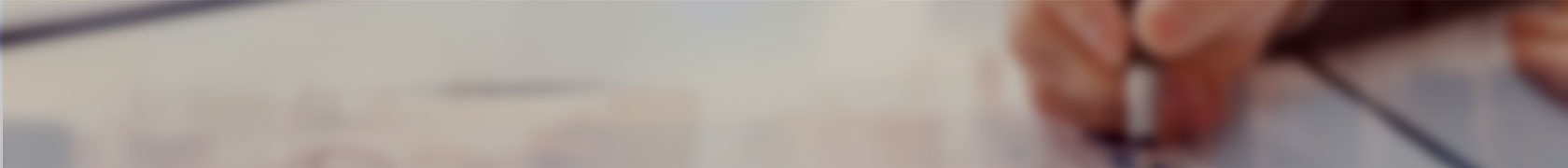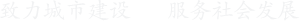我國要想從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的債務(wù)險(xiǎn)情,必須通過財(cái)稅側(cè)改革,實(shí)行“財(cái)政與稅收的重整”。這需要?jiǎng)?chuàng)立新的稅收思想與稅收框架:“增稅”不是主張盲目提高現(xiàn)有稅種的稅率,不是加重企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,而是以全新理念來支撐財(cái)政轉(zhuǎn)型。比如增加享受型和奢侈型產(chǎn)品的稅收,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,增加成熟工業(yè)品稅收,降低高科技產(chǎn)品稅收等等。
根據(jù)全國人大常委會(huì)會(huì)議審議國務(wù)院關(guān)于規(guī)范地方政府債務(wù)管理工作情況的報(bào)告透露的信息,目前全國“100多個(gè)市本級(jí)、400多個(gè)縣級(jí)的債務(wù)率超過100%”。按國際慣例,政府債務(wù)占GDP比例如超過60%就過了警戒線。我國正在推進(jìn)的地方政府債務(wù)置換及擴(kuò)大赤字,只是推遲了存量債務(wù)兌付的時(shí)間,不可能真正解決地方政府債務(wù)的質(zhì)量問題,要想從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的債務(wù)險(xiǎn)情,就必須通過財(cái)稅側(cè)改革,實(shí)行“財(cái)政與稅收的重整”。
綜觀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史,如果沒有財(cái)稅改革就很難走出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,一個(gè)國家走入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或是經(jīng)濟(jì)陷入停滯,很多時(shí)候都是因?yàn)檫@個(gè)國家的財(cái)稅增長無法跟隨上經(jīng)濟(jì)增長,無論是拉美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,還是東南亞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,抑或日本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,都是危機(jī)后沒有實(shí)行財(cái)稅改革,所以那些國家在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之后一蹶不振。
從根本上看,世界競(jìng)爭就是政策、制度的競(jìng)爭,哪個(gè)國家能創(chuàng)新出一套新的適應(yīng)時(shí)代發(fā)展的制度,那就將領(lǐng)導(dǎo)這個(gè)世界。當(dāng)年美國在羅斯福新政之后能走出大蕭條,一方面靠的是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政策,但最核心的還是因?yàn)榱_斯福重構(gòu)了美國財(cái)稅體系。在大蕭條之前,個(gè)人所得稅在美國是一個(gè)可以忽略不計(jì)的稅種,只是少數(shù)人才交;新政之后,個(gè)人所得稅成為美國第一大稅種;在大蕭條之前,美國沒有社會(huì)保障稅,大蕭條后社會(huì)保障稅成了美國的第二大稅種;羅斯福的財(cái)稅改革奠定了戰(zhàn)后資本主義長達(dá)三十年的黃金時(shí)代,而上世紀(jì)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減稅政策又將美國重新拖入了危機(jī)。
一國財(cái)政稅收必須與這個(gè)國家的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水平相適宜,一般情況下,純農(nóng)業(yè)國家的財(cái)政稅收占到這個(gè)國家GDP的10%左右是合適的,我國和歐洲的古代都是這種狀況;處于工業(yè)化初期的國家財(cái)政稅收占GDP的20%左右是合適的,今天,非洲和南亞的一些貧窮國家仍然處于這樣的稅收水平;一個(gè)走向全面工業(yè)化的發(fā)展中國家,財(cái)政稅收占GDP30%左右是合適的,而一個(gè)國家達(dá)到了中等收入水平,財(cái)政稅收一般要占到GDP的40%左右,發(fā)達(dá)國家的稅收一般占到了GDP的50%左右,北歐高福利國家則更高。
一個(gè)國家發(fā)展階段越高,稅收就會(huì)越高,這是因?yàn)樯鐣?huì)發(fā)展水平越高,社會(huì)分工越細(xì)致,國民對(duì)政府服務(wù)需求就會(huì)越多,也需要享受更高水平的社會(huì)福利、更優(yōu)質(zhì)的學(xué)校教育和更好的醫(yī)療水平。如果財(cái)政稅收體系不能支撐一個(gè)國家的發(fā)展,那必然會(huì)發(fā)生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。
第一次工業(yè)革命之后,在頻繁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和工人運(yùn)動(dòng)的逼迫下,人類建立了社會(huì)保障體系;第二次工業(yè)革命之后,人類建立了社會(huì)福利體系,財(cái)政稅收都相應(yīng)大幅提高;第三次工業(yè)革命至今,還沒有過大規(guī)模的財(cái)稅調(diào)整,所以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特別是政府債務(wù)危機(jī)頻頻。本輪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的核心就是債務(wù)危機(jī),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紀(jì)八十年代美國總統(tǒng)里根開啟的減稅潮,如果再繼續(xù)減稅,增加赤字,那將面臨巨大的利息支出,這些赤字利息將極大地?cái)D壓政府投資的空間,最終政府財(cái)政會(huì)走入“以債還債”的惡性循環(huán)。
我國正處于從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向全面城市社會(huì)轉(zhuǎn)型的時(shí)期,政府在城市建設(shè)和社會(huì)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(huì)增加,很難減少。我國本來是低稅收國家,2013年4月,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的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展望發(fā)布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,我國在188個(gè)IMF成員國中排名第146位。我國今天已成了中等收入國家,稅收占GDP比例也達(dá)到40%左右,這樣政府才會(huì)有足夠的財(cái)力去解決棘手的社會(huì)問題。
當(dāng)前世界各國所采用的稅收框架,基本上是上世紀(jì)三十年代大蕭條時(shí)期建立的,后來的“增稅”與“減稅”都是在這個(gè)框架不變的情況下調(diào)控稅率,但到了今天,如果還只是調(diào)控稅率,已完全無法解決問題了。因此,現(xiàn)在需要稅收思想與征稅方式的革命,創(chuàng)立新的稅收思想與稅收框架。在這種新的稅收思想下,“增稅”不是主張盲目提高現(xiàn)有稅種的稅率,不是加重企業(yè)負(fù)擔(dān),而是以全新理念來支撐財(cái)政轉(zhuǎn)型。依據(jù)這樣的思路,筆者對(duì)我國的“結(jié)構(gòu)性調(diào)稅”有如下四點(diǎn)建議。
第一,根據(jù)不同的行業(yè),不同的產(chǎn)品制定不同的標(biāo)準(zhǔn),將各種產(chǎn)品分為“生存必需品”,“享受型產(chǎn)品”、和“奢侈型產(chǎn)品”三類,提高享受型產(chǎn)品和奢侈品的稅收,降低生存必需品的稅收,甚至免稅,而奔馳、奧迪、寶馬等豪華汽車,以及一些名牌服飾、珠寶、化妝品等品牌可直接劃入奢侈品行列,這樣劃分之后,就可對(duì)這些產(chǎn)品進(jìn)行奢侈品認(rèn)定,增加征稅,增稅的空間非常大。
第二,將工業(yè)品分為成熟工業(yè)產(chǎn)品和新型科技產(chǎn)品,對(duì)成熟工業(yè)品可適當(dāng)提高稅收,因?yàn)槌墒旃I(yè)品需要投入研發(fā)的費(fèi)用非常少,只有生產(chǎn)費(fèi)用,而新型科技產(chǎn)品則需要持續(xù)的研發(fā)投入,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(shù)競(jìng)爭,可以降低稅收,以鼓勵(lì)創(chuàng)新。比如手機(jī)技術(shù)不成熟時(shí)可以賣一兩千,技術(shù)成熟后則賣兩三百,這就是成熟產(chǎn)品與非成熟產(chǎn)品的差異,成熟產(chǎn)品,價(jià)格低廉,可以適當(dāng)多征收稅收。
第三,對(duì)于產(chǎn)品,還可分為機(jī)器密集型和勞動(dòng)密集型,勞動(dòng)密集型產(chǎn)品可適當(dāng)減稅,機(jī)器密集型產(chǎn)品可適當(dāng)增稅,因?yàn)閷?duì)于那些已實(shí)現(xiàn)機(jī)械化大生產(chǎn)的產(chǎn)品,勞動(dòng)生產(chǎn)率非常高,價(jià)格也非常便宜,即使適度提高征稅標(biāo)準(zhǔn),價(jià)格也可以承受,而對(duì)勞動(dòng)密集型產(chǎn)品比如服裝、鞋則應(yīng)降低稅收,尤其那些更多需要手工勞動(dòng)的行業(yè)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發(fā)等行業(yè)理該減稅。
第四,考慮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(xiàng)稅收,降低公共稅收負(fù)擔(dān),增加專項(xiàng)稅收比重,能用專項(xiàng)稅費(fèi)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,政府提供的專項(xiàng)服務(wù)可適當(dāng)收費(fèi),政府在特定領(lǐng)域的建設(shè)也可通過專項(xiàng)稅收加以平衡,以降低公共稅收負(fù)擔(dān),進(jìn)而降低企業(yè)和個(gè)人的稅收負(fù)擔(dān)。